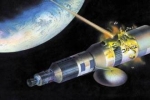解放军大将徐海东为何说“授我大将军衔有愧”(2)
一家被杀66口
1900年,父亲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(现大悟县)一个贫苦的窑工家庭。徐家六代都是烧窑的“窑工”。父亲有两个姐姐、五个哥哥,还有四个堂兄、一个堂姊,连同父母叔婶、侄儿侄女,一家32口人,却只有半亩地,六间房。他的童年,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和富家子弟的欺凌。
父亲曾告诉我,18岁前,他未曾吃过一顿饱饭或穿上一件新衣。从他懂事起,便跟着爷爷开始了长达11年的“窑工”生活。1925年春,父亲在同乡好友、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,毅然投身革命,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26年,北伐战争开始。父亲在被称为“铁军”的第四军中当代理排长,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。在汀泗桥战斗中,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了敌人四个连。父亲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,作战英勇、果断。不论再险再恶的战斗,他都能打胜,从此就有了“徐老虎”的威名。
1927年9月,父亲回乡了。他满怀革命热情,在家乡组织了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。1929年,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年关暴动。然而,父亲哪曾想,此举却让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暴动失败后,反动武装对父亲恨之入骨,进行疯狂反扑,先是烧了他家的房子,最后竟然将徐家66口人残忍杀害。父亲的27个近亲,39个远亲,男人全被杀光,女人多被卖掉,无一幸免。得知此事,父亲指天发誓:“大仇不报,誓不还家!”
1932年秋,红四方面军战备转移时,父亲受命狙击国民党的围剿。当时父亲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,哪怕全部牺牲,也要保障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胜利转移。当狙击任务胜利完成后,上级主力部队却和父亲失去了联系。在这种情况下,父亲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,他异常坚定,让士兵们吹响“集结号”,把掉队的战士、伤员和其他地方散兵全部组织起来,继续坚持在鄂豫皖苏区斗争。他们后来重新组建了红25军,父亲为军长,吴焕先同志为政委。1934年,红25军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担任“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任务。11月16日由河南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,经过湖北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等省,于1935年9月15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胜利会师。在这十个月当中,父亲与国民党奋战,每天都要进行四五次战斗。
母亲是不识字的“护理家”
我的母亲,这位从未上过学,个头不足1.5米,童养媳出身的女人,却让我充满敬佩。母亲12岁就参加了革命,她是个十分刚强的女人。1932年,母亲入伍到父亲的红25军战地医院当卫生员。1934年长征开始后,父亲军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:每人给8块大洋,投亲、靠友或者嫁人,部队不带女人长征。唯独母亲死活不走,在部队里哭,说什么也要参加长征。母亲曾裹过脚,是后来放开的,当时被叫做“改组派脚”。父亲后来在清点长征人数时发现她在哭,才得知是因为想要参加长征。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,决定将这7名女战士全部留下。这就是后来红25军长征“七仙女”之说的来历。
长征到了陕南,在庾家河战斗中,父亲负了重伤,枪从他的脸上打进去,从耳朵穿出来,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,昏迷了好多天。这也是父亲第9次负伤。当时,母亲被派去给父亲当看护,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慢慢有了感情。
长征结束后,母亲和父亲在陕北结婚。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,父亲接受新的任务,在敌后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。直到1938年底,父亲才凯旋归来。父亲后来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,1939年调入新四军。
1939年末,父亲抱病指挥部队,在皖西周家岗击溃了日军的一个大队。战后,他向干部作报告时,突然口吐鲜血倒地。此后6年多时间里,他一直是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的。
父亲身体不好,母亲那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照顾父亲。父亲肺部发炎时,一件薄衣服都不能贴着胸部,母亲特意做了一个铁丝架,把被子搭在架子上,父亲就这么平躺了6年。母亲每天都要给他做护理、按摩,父亲病那么重,南方那么热的天,他卧床6年从没有生过褥疮,没有生过痱子。我后来学医,才知道妈妈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护理家。
打仗有瘾,当官没瘾
1936年西安事变时,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。1939年5月,我在延安出生。9月,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。路上,刘少奇改用化名,扮成父亲的秘书,抱着四个月大的我,前往华东。此后的行军中,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,一头是我,一头是他,随着部队转移的。哥哥从小就很老实,爱学习。父亲虽然病了,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,很早就让他学认字,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。我想,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,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。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,上房子上树,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。我的性格像我爸爸,天不怕地不怕。但是有一条,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,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。上初中时,我获得三年全优,高中也是保送的。
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,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。
在大连,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。母亲说,孩子上学,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,过个节,或开联欢会时穿。父亲却说,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,你忘本。两个人吵了起来。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,要求我们也一样,即便家里吃饭,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,要全部吃光,从不允许掉一粒米。
1955年,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,翌年移住北京,并在党的“八大”上当选中央委员。而父亲却说,“我这个人打仗有瘾,走路有瘾,以前喝酒也有瘾,就是当官没有瘾”。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,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:“我一直养病,为党工作太少了,授我大将军衔,有愧啊!”
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,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。1958年,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,那一天,爸爸还给我改了名,叫徐红。他说,“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,你要做‘又红又专’的接班人,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。”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。
然而不久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我们如此“又红又专”的家庭也难逃厄运。
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,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,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,药不给了,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,拿针管……但没过多久,我就被关起来了。实际上,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。
几个月过去了,父亲常问母亲,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?母亲不敢讲,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。但没想到,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,一天,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:“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。”
“九大”之后,林彪发布一号令,1969年10月25日,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。那时天气非常寒冷,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,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,着了凉,引发了高烧。他们不让医院治疗,给父亲断了药,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。父亲患有气管炎,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,可偏偏派来个特务“秘书”,爆裂了暖气管。后来,整个屋子潮气很重,墙上都长出了绿毛,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。
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,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。这5个月中,他靠着坚强的毅力,一直在坚持,他想活着,想再见到毛主席;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1979年,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。
探望父亲的对手张学良
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,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,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。在我记忆中,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,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。我们在大连时,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。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,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。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,难以抹去。
2000年,张学良100周岁华诞时,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。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,不要向他详细提及我的父亲及其过往。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,我见到了张学良。当被告知我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时,不曾想,张学良准确地说道:“你是第15军团红25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。”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,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。
父亲曾说过,当年,张学良率东北军攻打红25军,他带了30万人的大部队追缴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。他们从何家冲一直打到陕北,走了10个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战斗,一天有时候就打四五仗,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了。长征到了1935年,爸爸的部队就歼灭了张学良3个师。国共合作后,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。其实,番号就是原来张学良师的,而缴获者就是我的父亲。
不打不相识。事过境迁,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,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。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,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面,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,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。他头脑很清楚,说要节约,不能大摆寿宴,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。
一年后,张学良逝世。那次见面,对于我们双方,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上一篇:上一篇:外媒:解放军将拥有5艘晋级核潜艇 打遍美国全境
下一篇:下一篇:普京突然卖给越南一致命武器 对解放军不怀好意
- 啪啪啪
- 女人图片黄一点图片
- 自慰
- 舔老婆
- 车震
- 马赛克
- 欧美
- 野战
- 真实
- xxoogif
- 美女被
- 肉图
- 办公室
- 39秒
- 不看后悔
- 有声
- 声音
- 狂射
- 无遮无挡
- 男上女下
- 狂日
- 贼好笑
- 强姧
- 男的和女的啪啪啪
- 嘿咻嘿咻
- 操逼
- 叉女人
- 大吴哥
- 出处
- qq天空网
- 邪恶吧
- 没内涵
- 大奶子
- 李毅吧
- 搞笑吧
- 后式入
- 动态图片吧
- 美女动态啪啪图
- 做嗳啪啪啪视频图
- 糗
- 口交
- 性绞
- 做爱
- 做僾
- 做艾
- 36D
- 天堂
- 成人gif
- av
- 潮吹
- 涩涩
- 揉胸
- 另类
- 黄色
- 福利
- 爱爱图片
- 后入式
- 27报
- 嘿咻
- 男女做爱
- h动态图
- 色你妹
- xxoo
- 撸管
- 露b
- 男人叉女人
- 卵蛋网
- 哈哈mx
- 性插图
- 电车痴汉
- 前入式
- 动态图
- 做爱动态图
- 啪啪
- 美女动态啪啪图
- 啪啪啪动态图
- 动图
- 美女动态图
- 操逼视频
- 美女动态
- 男女啪啪啪
- 邪恶的天堂
- 啪啪啪啪动态图
- 拍拍拍
- 啪啪啪动态
- 口绞姿动态图
- 邪恶萝莉
- 福利图
- av动态图
- 家教小故事
- caobi
- 女人自熨图片
- 邪恶gif动态图
- 黄色美女
- 邪恶动态图吸奶
- 邪恶美女
- 美女操逼
- 黄图片
- 叉叉叉
- 叼嘿
- 美女爱爱
- 女性图片
- 彩色漫画
- 动态美女图片
- gif出处高清视频
- gif动图
- 52kk
- 涩涩爱得得撸夜夜
- 动态插图很黄图片
- 27报
- xxoo
- 100经典出处gif动态图
- 邪恶gif
- 邪恶动态图27
- 操逼图
- 动态图出处及番号2017
- 美女动态图片
- 插图
- 邪恶动态图27报
- 美女做爱图片
- 啪啪啪gif
- gif邪恶动态图
- 口绞姿动态图
- 日比
- 邪恶帮
- 办公室诱惑
- 叉叉
- 028nb
- 黄色照片
- 邪恶动态图后式入叉
- 真人做爱
- 我爱爆
- 福利图片
- 干美女
- 福利动态图
- h动态图
- 动态黄图
- 美女口交
- xxoogif
- 爱爱图片全部过程图片
- 办公室偷吻
- 动态色图
- 邪恶少女漫画无翼鸟mhkk
- 操b图片
- 后进式
- 男女图片
- 美女自慰图片
- 美女黄色图片
- 美女自慰图
- 奶子图片
- 日本后式入动态图
- 邪恶动态图第五十七期
- xxo
- 邪恶集
- 邪恶动漫
- 邪恶古堡
- 邪恶色系漫画
- 邪恶少女
- 邪恶帝
- 邪恶爱
- 邪恶漫画无翼鸟
- 邪恶漫画大全
- 邪恶漫画基地
- 内涵漫画
- 色系军团
- 卡列漫画
- 幻啃漫画
- 美乳
- 美臀
- 黑丝
- 车模
- 裸身
- 粉嫩
- 比基尼
- 床照
- 空姐
- 超短裙
- 情趣内衣
- 白嫩
- 街拍
- 萝莉
- 少女
- 非主流
- 韩国
- 尤物
- 自拍
- 私房
- 长发
- 浴室
- 湿身
- 真空
- 时尚
- Cosplay
- 日本
- 巨乳
- 校花
- 古典
- 推女神
- 御姐
- 旗袍
- 学生妹
- AV女优
- 足球宝贝
- 网袜
- 丁字裤
- 熟女
- 白丝
- 人体艺术
- 腿模
- 台湾
- 短发
- 气质
- 少妇
- 女仆装
- 高跟
- 护士
- 女神
- 写真
- 性感
- 妹子
- 爆乳
- 情趣
- 大尺度
- 制服
- 清纯
- 酥胸
- 嫩模
- 翘臀
- 正妹
- 丰满
- 胸部
- 风骚
- 湿身
- 大奶
- 大波
- 长腿
- 可爱
- 小清新
- 学生
- 养眼
- 丝袜
- 胸器
- 童颜
- 透视
- 一字马
- 萌妹子
- 软妹子
- 主播
- 女仆
- 裸体
- 包养
- 后背摇
- 社会摇
- 丰臀
- 丰乳
- 纤腰
- 泳衣
- 女神撸
- 真实自拍
- 女警
- 快手福利视频
- 黑丝美腿
- 皮裤
-
1

中国太空轰炸机揭开面纱 引发国内外围观 中国的太空战机即将揭开面纱。(中国太空轰炸机快亮剑(梁天仞))而透露这个消息者就是梁天仞。《镜报》全球独家披露中国首艘航母初次试航...详细>>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